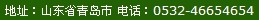|
奥数和补习班依旧处在话题风暴的中心,不但没能减少家长的焦虑,反而让选择变得更加困难。 作为二十年前的奥数状元、重点中学学霸,复旦学子,海归精英,作者肖蕊分享了她的亲身经历,以及对于奥数、儿童早期教育的反思。 夸张一点说,我的人生轨迹,曾经被奥数深深影响,这影响直至多年后也未曾完全消散。 越来越多,越来越小的孩子涌入奥数班 “奥数班”的历史其实远比今天大多数家长的认知更为久远,在国内一二线城市,奥数班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了。在“奥数班”出现之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,最火热的教育话题是“天才少年”、“科大少年班”、田晓菲……作为那个时代的年轻家长,我妈是那一套“早期智力开发”理论的拥护者,而我则理所当然地是这理论的试验品——入学前识字两千,会算数,有英语基础。 可以说,在当年我曾经是一个优秀的试验品,虽然现在这样的水平恐怕已经成了“幼升小”考察的基本标准了。 所以,当奥数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大规模出现时,我毫无悬念地成为了第一代的奥数儿童。在我小学三年级的夏天,“奥数班”(也称“奥赛班”、“特长班”等,培训学科不只有数学还有语文,以下为了方便统称“奥数班”)在我家乡城市的各区教研室一夜之间涌现。 各小学学习较好的孩子都应区里要求参加甄选考试,通过率并不高,至少当年我们小学,语文数学两门课都通过而得以参加的只有我一个人。 我童年的偶像田晓菲和她的先生、汉学家宇文所安,二十年后,我成为了田晓菲教授《秋水堂论金瓶梅》的一名普通读者于是,从那年的暑假开始,我的周末和寒暑假就被“奥数班”占据了。周末上午,假期整日,暑假至少四周,寒假则是两周,竞赛来临前还会加量突击,甚至需要向学校请假参加“奥数班”。总之,比起我的同学,我的假期大为缩水,作业量大幅增加。而区教研室,成了我在家和学校之外最熟悉的地方,我小学时期最深刻的记忆,就是一个人背着书包在学校与教研室之间“转场”。 小学的我,一个人走在九十年代夏天的柏油路面上,炎热而孤独。 而我在“奥数班”最快乐的回忆,是站在教研室的天台上,和一个留着假小子般短发的圆脸女孩,一起把练习本撕成碎片,做成许多迷你竹蜻蜓,一片片地放飞,看它们空中飞旋,想象那是六月艳阳下的漫天飞雪。那是我们在奥数的书山题海里的一点快乐自由——虽然那些纸片也不过只能飞短短的几秒钟,虽然那之前要谨慎观察之后要及时逃跑,因为扔一地纸屑,如果被老师或者保洁阿姨看到会挨骂的。 不过虽说是“书山题海”,“奥数班”的功课仍然称得上有趣。因为题目有难度,有挑战,解题方式也有很多的巧思。或者说,数学(还有语文)本来就是有趣的,学习自有学习的魅力。可惜“奥数班”的教学方式仍然属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,更多地北京中科医院是假的专治白癜风
|
时间:2018-7-1来源:本站原创作者:佚名
------分隔线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- 上一篇文章: 数学成绩老不好阶梯数学支个招,数学学习
- 下一篇文章: 那些征战股市的工业软件公司